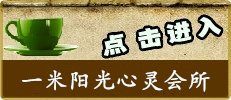罗杰来到研究所的咨询中心寻求帮助。经过初次接诊后,罗杰同意参加一个为期10周的、免费的治疗前培训班。 罗杰不久前刚满36岁,他的主要不适是广场恐怖,并在过去12年中逐渐加重。此外,接诊记录表明,罗杰还大量饮酒、超重、对工作不满意(他一直在忍受严重的焦虑以保持工作)、多种恐怖症,并且是一个活跃的同性恋者。罗杰对他的性取向并未要求治疗,他认为这不是一个问题,他要求治疗的是广场恐怖,因为这妨碍了他与同性恋伙伴交往。 第一次治疗:建立治疗关系,明确问题所在。 本次治疗由莫萨克展开,试图澄清问题。 治疗师:好,是什么使你来到研究所的呢? 咨客:我出了点问题。我想他们叫它广场恐怖症,就是害怕到空旷的地方去。在过去10年或是12年中,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现在,这种情形几乎 到了让我无法生活的地步。 治疗师:这就是你带了一个朋友来的原因吗? 咨 客:是的,有个人跟我一块儿来。 这个一块儿来的朋友使得罗杰能够外出。罗杰接着解释说,如果他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他的焦虑就不会如此强烈,因为这样的话至少他可以预先避开那些引发他恐惧的地方。在他出门前,他还以饮酒来对付自己的焦虑。 咨客:……我想这主要是一种不安全感。过去一年里我换了三次工作,上周我又开始做一份新的工作。在去那儿上班前的一个星期里我都很不安,一直为要到一个新的环境中去而担心。对于开车去那儿我怕得要死……我都是由弟弟开车接送。但是在那儿呆了一星期后,我开始自己上下班,现在已经有两天了。不过我还是整天为下班发愁……是否会撞车。我总在那儿担心会出交通事故。那样我会惊惶失措。这种想法使我很恐惧。 治疗师:由于你的症状,使得你可以让别人为你做事,这你已经说过两次了。一是你让一个朋友陪你来这儿,二是有一周的时间你让你的弟弟开车接送你上下班。听起来你对此很无能为力。 个体心理学是一种实用心理学,它侧重个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例如,阿德勒派从不说某人脾气不好,而是说某人以自己的性格来胁迫别人。坏脾气是个体用来达到他的意图的手段。在罗杰的病例中,莫萨克对症状作了重新疏理(Reframe),以此来显示这种手段是如何被应用的:罗杰让别人为他服务,虽然他可能全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他对此负有责任。 治疗师:在过去12年里你对此(广场恐怖)做过些什么? 咨客:嗯,我尽我所能来对付它……避开某些特定的事情,避开某些特定的地方,不到树林里去,不去度假,总之不干许多正常人会干的事。 阿德勒认为,神经症可以看作是对生活任务的逃避。罗杰把他的生活局限于他自己能控制的范围内。实际上他是在说,他只有在感到安全时才行动自如。 治疗师:哦,但实际上那样并不解决问题。那是一种被你自己的症状所限制的生活……你是否试过克服你的症状呢? 咨客:是的,我曾找过城里的一个精神科大夫,他给我服用氯丙嗪,那让我很不舒服,后来就再没有找过他。老实说,他让我很紧张……他实际上对我的问题并不太关心。他对我这样解释:“看起来你主要对你自己感兴趣……我认为你是个自我中心的人。”那种态度令我不快……他太不重视我了——总之,我们合不来。 罗杰这话的含义十分明确,他是在警告这位新的治疗师:你必须认真对待我的问题和我本人,否则我不会再来。实际上,他是在说他需要别人关注他。要是他感觉其他人并不关注他,他就会以自己固有的生活方式来行事——他会“紧张”并且避开他们(正如他对以前的那位治疗师所做的)。罗杰觉得那位治疗师不理解自己。 治疗师:如果我有一根魔棍,我把这根魔棍在你头上挥几下就可以把你的广场恐怖症去掉……那样的话你的生活会有什么不同? 这是阿德勒派的设问法(The Question),可以用来判断症状的目的,也可以用来区分躯体障碍与心理障碍。它通常预示着所逃避的东西——即产生这种症状有什么意图。 咨客:那样的话,就会消除许多预先做计划所带来的恐惧和挫折。你知道,我必须计划我一周的生活……我必须安排好朋友接送我上下班……我完全可以轻轻松松,尽情享受生活……我必须放弃一些好的工作,因为我害怕乘飞机。 治疗师:设想我让你采纳一个计划,你和我一道坐飞机去洛杉矶?设想我会照顾你的一切事务? 咨 客:你会的。 罗杰没料到,他已经对莫萨克道出了他的广场恐怖症的目的:他想获得控制。如果没有他的症状,他就不必预先做计划,也不会让其他人来照顾他。这些症状使得他有借口对别人指手划脚,并让别人为他服务。 本次治疗剩下的时间用于对生活任务进行探讨。个体在每一项生活任务中的运作情况显示出他们的社会趣旨达到了怎样的程度。罗杰这样评价自己: 工作:很差。他必须指挥与他共事的人。他的症状已经开始影响到他作为运输公司经理人的职位。他每天早上都要喝酒才能去上班。 友谊:他的友谊主要来自于他的同性恋交往,他的广场恐怖症也对此有影响。 爱情:他订过一次婚,但女方解除了婚约。他从未与女性有过性关系,但与男性的性关系却很频繁。罗杰声称这方面不是问题。 自身(self):罗杰认为他还算得上一个不错的人,但他对自己的体重不满意。罗杰补充说,他“不喜欢自己”——他觉得“内心很丑”。他还担心成为酒鬼。 精神(spiritual):罗杰从小被培养成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现在仍然祈祷,在家点蜡烛,但因为他的性取向,他不愿忏悔。当他声称“我不需要忏悔”时,莫萨克说:“连教皇都需要一个忏悔神父。”罗杰毫无幽默感地回答说:“他比我更需要。” 治疗结束时,治疗师对罗杰给予了鼓励。罗杰感到,36岁还要着手去做其它很多事情“太晚了”。他毫不隐瞒地说,他对自己感到失望,对自己没有能力超越自己的生活感到沮丧。莫萨克提到过去的一位同事,这位同事直到47岁才去读医学研究院。但是,罗杰只想带着他的广场恐怖症去工作,他非常怀疑他克服这种症状的能力。 此次访谈以治疗师安排下两次治疗为结束,这是一项对于控制者特别有用的技术。罗杰将与一名合作治疗师会谈,这位合作治疗师会用一份“生活方式评定表”收集资料,阿德勒派用这种方式来了解咨客的各种目标、意图和基本的领悟(apperception)。同时,莫萨克毫不含糊地说明,他在治疗过程中处于控制地位,他在对治疗的控制中尊重罗杰的各种要求。 总的来说,罗杰是一个控制者,他用被动的方式控制别人。36岁时,罗杰的被动控制方式(通过广场恐怖症)引发的负效应让他再也无法忍受,于是他开始求治。他有强烈的自卑感,社会趣旨发展不完善,这可以从他的整个状态看出来,那就是他对各项生活任务的完成情况都很糟。尽管他的自我评价(self-concept)不好,他仍然认为自己有一定的优势(他比教皇优越)。治疗师已经向罗杰表明他理解罗杰的问题,他重视这些问题,他会尽量把自己的目标与咨客的目标统一起来,这样就减小了治疗阻抗。最重要的是,罗杰非常沮丧,而他鼓励了罗杰,并给予他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