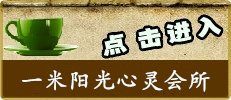心理咨询情景自然会引出来访者的爱。事实上,Martin Bergmann观察到它以这样一种可靠的方式运作:“几个世纪以来,男人和女人都搜寻可酿制爱情药水的曼德拉草的根和其他物质。然后。。。。。。维也纳的一个犹太医生发现了爱的秘密。”这个秘密就是仔细倾听,真诚地对其他人感兴趣,以接纳且无羞愧的方式对他/她的披露做出反应,并不要求对方满足自己的情感需求——这定义了精神分析设置的方方面面。
人们早就知道,许多病人已爱上或者将会爱上他们的治疗师。治疗师们爱上他们的许多病人却很少被高调宣传,虽然从有关心理治疗的电影可以推断出治疗师有一定数量这方面的幻想。事实上,精神分析文献里认为我们很少爱上我们的来访者,而关于我们的爱是主要的治疗手段的意见则更加罕见。实际上有一些精神分析认识对爱能治愈的想法感到不屑。科胡特的理论不止一次被批判的理由是,他的思想课归结为试图通过分析师的爱来治愈病人,因此其本身是令人怀疑的。
但有迹象表明,以L打头的这个字即将解禁。老早以前在我准备出版这本书的时候,两位在治疗过程中采取主体间性与呼应性的分析师们发表了两篇开创性的文章,讨论关于爱在治疗中的角色。Joseph Natterson建议,我们应把心理治疗看作“互爱的过程”,在其中治疗师的“次级主体”通过欲望、信念和希望的自然进展,随着病人自体的现实化培养病人爱的现实化。丹尼尔·肖在注意到精神分析作家已经扭扭捏捏地提出他们对自己病人的爱的问题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分析之爱”可能是治愈的一个关键因素,不过他把“分析之爱”与浪漫之爱、性之爱、反移情之爱做了区分。肖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精神分析为分析过程提供了一个仪式化的设置,这个过程会鼓励被分析者发展对他们自己的亲密意识。在此过程中,分析师和被分析这不可避免地也是必要地在智力和情感上彼此密切卷入。这一努力的核心。。。。。。是对爱、被爱、给予爱和接受爱的受挫能力的再度活化的寻求。除了考虑我们的职业选择以外,这看起来更合适描述被分析这而不是分析师。我们之所以选择我们的工作,是不是因为,至少是部分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现实这个目标的手段呢?即让我们对我们的被分析者来说特别重要——尤其是被他们爱和尊重?
我想补充一点,作为治疗师,为我们提供体验爱着的自己的机会,一种本质上有益于自尊的精神状态。如Racker所指出的,本质上促进治疗的爱的态度也可以通过象征性地补偿早年爱的客体而消除我们的内疚,我们潜意识中相信我们曾经伤害过他们。
心理治疗的实证研修越来越清楚地表明是关系带来了治愈。但“关系”有点抽象。其中一人带着痛苦进入这个关系,离开是感觉症状减少、更有活力、更有自主感、更真实了,这两个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神经心理学研究正在揭示,客观上,当我们保持与他人亲密感的情感接触是,我们各自的大脑会发生改变。但主观上,在咨访二元关系中,看来确实已经产生了爱,并被来访者吸收而产生了疗效。我认为Bergmann是正确的,他认为最初激发病人对治疗师的爱,是治疗师既与童年照顾者相似又与其不同的感觉。当治疗联盟建立后,往往是治疗师与父母不同的方式给来访者带来最有力的触动。